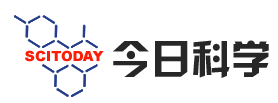高校青年教师“压力地图”一瞥
中国科学报记者 温才妃
18年前,某高校青年教师在媒体上以“青椒”自嘲,感慨工作、生活压力之大。18年后,又一代高校青年教师在“双一流”建设、“破五唯”改革、“非升即走”等背景下,迎来新一波压力峰值。
压力之下,谁在“内卷”,谁在“躺平”?如果将处于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高校教师所承受的压力绘制成一张“压力地图”,我们会发现,这张“地图”的压力分层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越好的大学教师压力越大,而是压力感受与高校“上进心”成正比。
事实上,最受煎熬的是力争“跃层”的高校教师,其次才是稳定发展的高校教师,而失去竞争动力的高校教师已部分“躺平”。
在顶尖高校做一名“六边形战士”
在外人眼中,顶尖高校教师将主要精力用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科研无可厚非,但身在北京某顶尖高校的青年教师陈岚却明显感到“不是这样”。
这是一所定位为冲击世界一流的高校,在国内高校中地位稳定,其竞技场也早已由国内转至国际,能否在世界一流高校梯队中再上一层楼是它关心的事。
该校的教师“预聘—长聘”制更多参考国外高校的教研序列。而且,该校的传统是科研、教学“双肩挑”,社会服务也不能少。闲聊时,教师们都戏称自己为“六边形战士”。
学校对教研岗位的要求是4:4:2,即科研、教学占四成,社会服务(主要是校内行政工作和学术服务工作)占两成。但实际上,陈岚白天工作时的精力分配是2:5:3,科研占两成、教学占五成,社会服务占三成。
明年是陈岚“预聘-长聘”制的最后一年,但分配给与“非升即走”最相关的科研的精力却最少。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她能力超群或怠慢科研,而是其他工作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
“备课、授课、答疑、指导学生论文占了我一半时间。”她告诉《中国科学报》。
陈岚有一门难度较大的秋季学期课程,“每年都会在备课上花费很多心思。”但比起春季学期,她在授课的同时还要操心学生的论文送审、毕业答辩……即使秋季学期堪称“轻松”,她也明显感到春季学期比秋季学期更容易动肝火。
“开始时,我让学生自由选题,范围只要在大领域内就可以。但我发现,辛辛苦苦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后,学生进步很大,但我的科研却没有什么进展。”陈岚说,这两年她调整了策略,“我发现做得比较好的教师,是把学生论文与自身科研方向紧密结合。这样,他们在指导学生的同时,自身科研水平也会有所提升”。
陈岚还身兼学院学生管理的工作。于是,在她工作时,时不时就会有学生过来签字,或电话通知她和学生谈心,处理学生的心理危机。刚坐下来不久,又接到安排学生奖学金、助学金、贷款的评定任务;还有学生党建、纪律处分等工作等着她,一叠叠文件袋摞满了桌头。“特别是疫情期间,更是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学生管理工作中。”
此前,她还加入了教学委员会,在学校职能部门挂过职。
“感觉自己的时间就像一块布条,被零零散散的事情撕得粉碎,很难静下心做一件事。”陈岚说。
教研系列的教师为何要从事行政工作?也有教师不解,甚至公开质疑过学校的做法。但“学校一直将其视作一个培养青年教师的过程。鼓励教师不只待在书斋,还要到社会上看一看。那么,学校首先就是一个小社会。”陈岚换位思考。
只是自己的“晋升”大事,被迫排在了最后。
孩子出生前,她的科研基本被安排在晚上。有了孩子后,晚上时间不好安排,只好集中安排在某几天。“我把会议集中安排在下午,上午空出来做科研”,但很多会议时间不是她说了算,只能被动接受安排。
于是,包括她在内,高校教师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晚。时常在凌晨一两点,她还揉着眼睛在台灯下查资料、写论文。
熬夜搞科研、周末搞科研,是不少高校教师的常态。
陈岚的父亲也是高校教师,他当年同样如此,在全家人睡觉后才开始科研工作,且退休多年依然保持这个习惯。
熬夜伤身体,很多教师也为此担心。陈岚有部分同事习惯早上四五点爬起来搞科研。“感觉他们睡五六个小时就够了,但我至少要7个小时才能睡饱。”上学期她尝试每天睡五六个小时,但不时就会有困意袭来。“难怪校园里的咖啡越卖越好。” 她打趣道。
寒暑假是很好的补觉时间。但刚放假时,因为“习惯了工作时的生物钟”,她还是会在一大早醒来,直到一周后,醒的时间才越来越晚。
想到“非升即走”,陈岚还是一阵紧张。但比起一些高淘汰率的高校,她觉得还算幸运。“起码学校不以淘汰为目的,我的努力会被大家看到,大家也在帮我想办法,告诉我该往何处发力。”
出走,她成为不孤单的“孤勇者”
去年冬天,不少南方人选择到东北当一次“南方小土豆”。但张敏却逆向而行,离开了东北某“双一流”高校,到广东一所高校任教。
她离开的高校处在“双一流”高校的中上游,近年来为了再跃一个台阶,可谓下了“血本”。
“长聘副教授的年薪45万元,长聘教授的年薪60万元。”当学校“预聘-长聘”制的“盲盒”被打开,几乎所有教师都惊呆了。“稳定的穷”是事业编制教师的常态,15万元、20万元分别是副教授与教授年收入的标配。但以2020年入职为界,学校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区别对待事业编制教师与“预聘-长聘”制教师。
这一下,教师群体骚动了。
“我可不可以转到‘预聘-长聘’制,按‘非升即走’晋升?”和很多教师一样,张敏咨询过人事处,得到的答案是“不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某位新教师走的是“预聘-长聘”制,但他偏“佛系”,不喜竞争。“我能否走老体制,不要‘非升即走’?”人事处的回复同样是“不行”。
双方陷入了“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可是一条不太通“情理”的规定横亘在他们中间。
“博士毕业要事业编,赶紧去新疆高校找工作,那里没有‘非升即走’,还是一片‘净土’。”张敏无奈地给学生支招。
如若不然,就要抱紧学术大咖的“大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东风发现,不少优秀青年教师没过几年就会离开学校。“因为单打独斗基本上没有‘升’的可能,只有背靠‘大树’,才能在国家课题、重点项目等竞争中分一杯羹。”
既然体制不可兼容,张敏只能硬着头皮去晋升。此时,她发现在“非升即走”的助推下,一切都变了——前年,评教授的标准还是5年一项国家课题,去年便被调整为5年内两项国家课题。而且,整个文科大类有且只有一个教授晋升名额。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用高强度的竞争激励教师出成果。对此,张敏可以理解,但制定规则的领导们,当年可是以省级重点课题获评教授的,以标准水涨船高、事业编制有限为理由,制定几乎难以达到的标准,掩盖的是事实上的不公平。须知,有的教师穷尽一生也拿不到一项国家级课题。
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例,2022—2023年度,全国终审通过率只有13%左右。有教育学者做过估算,如果从学校初审开始计算,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淘汰率大于95%,部分学科申报立项比甚至连2%都不到。
果然,5年内两项国家课题的标准一出,偌大的文科学院内,百十来号人都傻了眼——他们中竟没有一人符合标准。
其他的晋升标准也水涨船高。此前,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可算积分,积分达10分以上可参评;如今,只有发在顶刊上的论文才算积分,发在SCI期刊、CSSCI期刊、核心期刊、普通期刊上的论文统统不作数。被砍掉的积分挪到了咨政建言等方面。
“‘破五唯’本没有错,只是进程无法更快,致使制度还没有稳定下来又回到了起点,甚至变本加厉。”张敏说。
晋升无门、稳定的穷、事实上的不公……张敏感到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憋闷不已。“学校发展想用增量代替存量,我们主动给他们腾位子。”言语之间,她满是心酸。
决定“南下”后,张敏发现自己并不孤单。一年之内,该校离职的教授竟有百余名。但反过来看,作为人口流出地区,东北高校要在短期内招聘百余名优秀教师,显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无论是离职教师还是新进教师,一夜之间仿佛都回到了原点。
由于晋升标准一致,面对这一几乎无法达到的新标准,按“预聘-长聘”制进入学校的新教师同样看不到希望。大家思忖着,大概率5年后还要重新找工作。
到新单位后,张敏如愿进入了“预聘-长聘”制,但身边同事都特别优秀。成不了“卷王之王”,“5年后,‘走’的可能性远比‘升’大”。
然而,张敏宁可被其他高校“割韭菜”也要跳出来,就像是一名悲壮的孤勇者。“我的学术出身还不错,如果被淘汰了,最起码人在大湾区,熟悉了当地的高等教育环境,日后可以选择在一些地方院校任教。”
如果广州、深圳实在留不下来,下一站张敏想去海南,“我希望所在城市处于高等教育跃迁式大发展阶段。我必须找到这样的城市,才能有更多发展机会”。
她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教授梦,晚几年实现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所在高校要有组织地支持我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被迫躺平”的教师
中部某地方院校教师周林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为“躺平式教师”。在他的心中,“躺平式教师”是那种一朝成为教授,便不再搞学术、不再写书,平日只愿凑足工分,健身、遛鸟、假期带着家人游山玩水的人。
“他们太疲惫了,一辈子都在为指标奋斗。”周林说,热点在哪里,他们就扑到哪里;为拿课题而四处打点;平时还要和领导、学术期刊编辑搞好关系。总被退稿,总在PK。内心的煎熬如同高考完把书撕烂的考生;其疯狂状宛如现代版的“范进中举”。
然而扪心自问:“自己的奋斗目标又是什么?似乎还是职称。”周林也曾想有所作为,但无奈学校的科研水平总体不高,省级课题尚能够着,教育部课题、国家级课题却只是“奢望”。
回想十多年前,他在入职之初也曾积极参加教学竞赛,并拿过市里的一等奖;风风火火地带学生去外地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还当过班主任,像自己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他让自己忙得像个陀螺,却总是被同事笑作“傻”,因为“这些都是良心活儿,很少能给评职称加分”。
年近四十,他依然是一名讲师。那些“聪明人”则在标准尚未提升时,通过发论文、拿课题而成功“突围”。
当学术进取的“潮水”退去,剩下的只有生活的一地鸡毛。身边,与自己同龄却未“突围”的教师,要么躺平了,要么另谋副业。
周林的一些女同事总是在晒娃,今天带娃参加网球比赛,明天陪孩子参加电视台舞蹈表演。她们已基本放弃晋升念头,而是将重心转向培养孩子,到点接送,晚间、周末辅导,送孩子参加比赛、游学,很少出现在加班人群中。
还有的教师心思活泛,有体育、音乐、书法等一技之长的兼职做起各类培训,一年赚的外快比工资还高;有教师办起了高考、公务员考试、资格证培训班,课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些人还成了“网红”教师。
周林的日常也变成了家、孩子学校与单位“三点一线”式机械摆动。“被迫躺平”让他多次质疑工作的意义。想努力却没有方向,想换环境却缺少离职勇气,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令他懊恼不已。
“不知道每天都干了什么,仿佛只为了凑够工分。即便是上课,教师们开课的目的也是为了凑工分,一门国学选修课,谁的工分不够谁就上,讲台上的面孔犹如走马灯一样,新闻学、经济学、艺术学、思政课等,几乎全校教师都上过。教育学教师还开起了书法课。“搞得我们一点专业归属感都没有。”
心心念念的职称越发遥不可及。周林所在的学校属于新建本科院校,职称评定还在省里、未下放到高校,看的还是论文、项目。一年到头,单是评副高的校内老师就有几十号。
“遥遥无期更加速了教师们的‘躺平’。”温州大学副教授王硕旺说,当躺平式教师越来越多,也就有了躺平式高校。
他指出,特别是1998年以后取得本科身份的新建本科院校,其发展动力不足,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平跟不上。大量中部、西部的地方院校,尤其是非省会的地方院校,也陷入“被迫躺平”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被迫躺平”还有更大隐患——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周林有强烈的生源危机感,“没准儿哪一天,教师就可能因为无学生可教而下岗”。
近年来,在“破五唯”的推动下,某些地方院校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比如周林同城的一所高校去年进行了改革,“年终考核工分认定的内容更加丰富”。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加10分、一本专著加50分、作一场学术报告加2分、做一个培训项目加2分、做一个100万元的横向课题加15分。制度的设定“鼓励教师人尽其才,做什么都有回报”。
但他希望“改变的力度再大一点”,“先把职称评定下放到学校”。
| 分享1 |